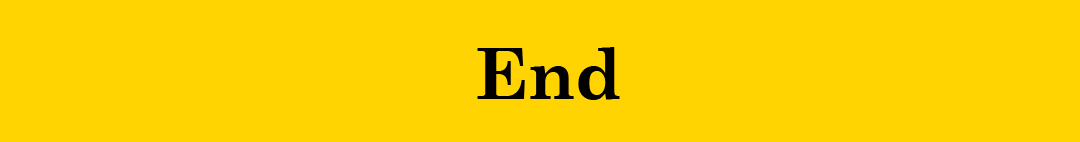人群,筑墅别悲欢国画 / 2021
图文: by 收藏家 于迎春
代英伦的水墨作品具有鲜明的辨识度
他以独特的题材内容和绘画语言
建构起一个个性化的艺术世界

研究生毕业之后,2017年,代英伦正式将“人群”确立为自己的系列性表现主题。几年以来,他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开掘这一内容。
“人群很有意思,是人作为人的宿命。每个人都会在一个人群中存活,人群有大有小,但都改变着个体同时又被个体改变。我冥冥中感到,人群,无论是什么样的高尚组织还是偶然聚在一起的穿过马路的人们,如果缩得足够小离得足够远来观察,那都无非是在做布朗运动的小点。这是我之所以想要解构所有有意义的事物的原因。……在我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如同一个谜,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源头,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代英伦《自述》)
显然,“人群”对艺术家来说,有表达不尽的情境和意味,给了他充分的表现空间和满足感。画面中总是聚集着一群人,他们常常步调一致地进行着某项共同性的活动,成群结队地现身于某个场景。
同时,
画家赋予了他们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
无论他们的装束是古是今,
无论他们是赤裸还是半裸,
容或他们的发式、服饰、行为、姿势有别,
但他们宽额阔面、四肢纤细的模样
看起来非常相似,俗称对眼的内斜视,
则使得这些人物群象初看上去不免有些滑稽。
这些人物的眼神,那种专注而狭隘、
顾盼而疑虑的眼神,最大可能地呈现了
人群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状态。
带着千篇一律的趋同面目,
这些群体中的个人,
已经很难说是以独立自主的个体面貌而存在着。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
他们相互交流、理解,
进入彼此的悲欢,
在感觉不被抛弃、不孤单的同时,
他们却也在群体化的均平效应中,
失去了个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除了性别,在这些成群的成年人身上,
几乎不显示他们的职业、
性格、爱好、生活方式、
教育状况等更多的个人特点,
大多时候,
他们表现出一种基本类似的表情
和相似度极高的神态,
比如茫然不解、犹疑不定、困惑无头绪。
他们从事着一些不可思议的集体活动,
但似乎对其中的意义缺乏知觉;
即使被笼罩在同一气氛中,
看起来却是散漫而各怀心思。

人群,扇动起希望在起风之时 / 2020
在这个并不存在的世界里,
代英伦导演着以人群为主角的
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

画中有许多情节性的描绘,
在红色的宫墙下逡巡,
在屋顶或者云间翻滚,与游鱼在空中并峙
凝视水中的倒影,飞翔于水面,
乘着骨头制作的小舟渡越波涛.......等等。
在大面积纯色的背景上,这些看起来颇具游戏、趣味感的情节,具有了某种抽象性:缺乏具体的时空因素,置身于不合理的情境,这一切都是为了构筑一个非真实的世界。
这些聚集成群的人,
象棋子般排兵列阵似地聆听训诫;
或者在整齐的严肃队伍中,
有人反常规地做出了倒立的姿势;
攀爬高墙以试图越过权力或者阶层的阻隔;
骑着木马、木龙却打算乘风破浪而行……
他们有时手持不合时宜的,
彼此不一定有关联的道具;
有时处于奇特的场所,
如岩洞、云间、江海波涛之中。
这些时时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道具、行为,
画家一本正经地描绘它们,
只是为了传达其中难以言说的荒诞感,
或者在荒诞、错位中放大、凸显
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浑然不知觉的庸常、虚幻、非理性。
当然有时候,这位异想天开的艺术家,
或许只是随手选用了一些元素
作为画面构成的点缀,
或者用作其中的戏谑、调侃。

人群,实则随机的有目的寻找行动
人群,并非自由的、独立的、
个人的简单集合,
人群的特点也绝不是
其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特点的叠加。

他们的聚集,无论是暂时还是持久,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因为理想还是利益,是因为宗教还是乡土,是因为职业还是圈层,每一个个体,都注定是各种不同人群的一员,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人能群。”“人生不能无群。”
(《荀子•王制》)
但是自我与社会、个人与集群,两者关系复杂、微妙,既排斥、抗拒,又无法脱离。
叔本华曾用刺猬的比喻,
生动地诠释了个人与人群的关系困境:
刺猬靠近彼此以相互取暖,但它们身上天然存在的长刺刺伤了对方,以致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反过来又使它们难免感觉寒冷、寂寞。
人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存在者,生活是他自己的,生老病死是他自己的,谁也代替不了;但是每一个个体又都无法孤立存在,他人必然会影响到个体原本自由、主体的特性。
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论断,更为系统、
深刻地阐释了自我与他人的矛盾关系:
他人是自我存在的证据,通过他人的目光和评价,我们得以认识自我;但也正是因为他人的存在,并以他人的眼光,作为评判、认识自我的标准,自我就常常会被影响、左右,难以坚持,甚至被迫做出自己不情愿的选择。
事实上,冲突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种族、宗教、性别、国家之间。说到底,人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彼此理解、接纳?人群对于我们如何可能不伴随着伤害?我们将如何展开有质量的社会生活?在艺术家的揭示下,一切都有了诘问的必要。
代英伦笔下的“人群”,
不同于勒庞所谓的“群体”,
后者在著名的《乌合之众》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了“受群体精神统一定律的支配”的组织化的“群体”。
代英伦的“人群”要更宽泛,
更不受限定,
那些人可能只是偶然地彼此站在一起,
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感情上的目标。
简言之,画家不是为社会心理学做注脚;
人群,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对于群众、人民的考察。
毋宁说,“人群”乃是代英伦基于对眼前现实社会生活的观察,更基于对自我以及自我情绪的审视,经过不断反思,将内心感知、想法具象化所转换成的图像。
艺术的表现虽然有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和知识、信仰为基础,但它更直接依赖于艺术家在个体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体验,他的艺术灵感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和思考,并被后者所激发。
生活有多么纷繁多样、
人性有多么微妙复杂、
人的意识有多么错综难言,
人群就有多么变化多端。
因此,代英伦揭示人群的盲从、驯服、压抑、单一性、人云亦云,但是他并不把人群简单地等同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偏执特性。他希望观察那在漫长历史和文化中,芸芸众生所积淀下来的千姿百态,包括他们那被隐没的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并在对无意识的社会行为的正视中,披露我们在走向现代文明的长期过程中的积弊和局限。
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里已经积攒下太多概念、主义、规定、原则、价值,所有这一切文化传统,都足以把人异化,令人在长期的学习和潜移默化的规训中不知所措,从而丧失了对真实、自然的存在的体认。

人群,乘风国画 / 2020
“人群”是代英伦表达他对于自我、人生、社会的感受和认知的载体、渠道。
“每个人心海中恒河沙那么多的意识,每个单独的意识凑在一起组成了画面。同时,那些人们,或喜或悲或忧或怒组成了人群。”(代英伦《自述》)
表现个体主观世界的复杂性,表现内心中多重意识和思维交织的矛盾、冲突,如此,“人群”就不啻是被观察的客体,它也成为了艺术家本人的多重意识所藉以外化的群体形象。
《巴黎的忧郁》中有一篇《人群》,
波德莱尔在其中写到,
融入人群之中是一门艺术,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做到:
“人群与孤独,对一位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是两个同义、可互换的词汇。若无法将自身的孤独巧妙地融入人群,就无法在繁闹的人群中保持孤独。/诗人独享了这项无与伦比的特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自己或他人。如同那些寻找躯壳的游魂,若他愿意,他可以进入任何人之内、融入对方的身分与角色。”
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及因此而来的批判性思考,又能够体察、表现众生的心态和面貌,这来自于艺术家令人钦羡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难能可贵的是,代英伦抱持了显而易见的非精英意识。他把自己放在其中省察、剖析。
“我渐渐觉得,其实我所认真描绘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其实都是我内心投射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一部分。他们——那些画面中的人,每个人都代表了一部分的我,可以说是一小部分的我,而同时也许还代表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包括死了的和没来的人。……我笔下的这些男男女女,都是一个整体意识当中的微小侧面,都是一个单独的小念头、小情绪、小观念。正是这么多的情愫和状态,组成了复杂到我们自己也很难认知的自己。”(代英伦《自述》)
因此,画家的审视是平和、温情的,他有揶揄、批评、批判,但他充满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使他只在相对平衡的社会状态下,展现人群最普遍的可能性,在温饱、安全之上的可能性。
代英伦曾经在哲学思辨和宗教学理中孜孜以求精神上的寄托和觉悟,现在他分明更希望通过世俗化的日常图景来表现生活或显现或潜隐的方面。与早先带有明显哲理意味的偏于灰冷的画面色调有所不同,他逐渐开始采用更丰富、鲜活的人生场景和元素。
“怆然大会”、“华丽的遗蜕”中,众人围拢着,在盛开的鲜花与枯骨之间谛视聆听,歌乐鼓舞并行,黑、红两色通贯画面上下,在如此醒目的背景中,这个有关生死领悟的场面已足够令人惊艳、惊觉了。
生死、寿夭、有无、时间、幻梦、权威、个人意志、人的自我禁锢与自由,代英伦将这些终极问题尽可能日常化,以清通易懂的形象,传达出生存、生命的别具一格的发现和感悟。于寻常处用心,这种举重若轻的自信态度,表明了艺术家的成熟。

人群,华丽的遗蜕 / 2021
代英伦的绘画艺术也在日趋成熟。
在对自我语言不断的探索、尝试中,
形象、图式、笔墨、风格,
在阶段性的稳定之后,
往往会发生某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总的说来,他的自我概括逐步完善,
绘画语言也越来越自由。
与先前较为定型的人物相比,现在的形象看起来更随意、自在,也更具多样性;人物的组织、调度,场景的安置、铺排,也显得更为从容、自然。寒鸦、云朵、骷髅、伞、华盖、枯树、荷叶,这些他早期作品中带有明显隐喻性的物象逐渐减少,不再密集地出现。随着画面元素、层次的丰富,所传递的情绪、意涵则越来越浑厚、耐人寻味,难以明确地加以界定。
代英伦以“人群”为代表的作品,
是与传统的水墨主题、图式、趣味、
格调非常不同的现代表达。
他的系列创作仍处在令人好奇的发展过程中,很难预知他下一幅作品的面貌,这种变化莫测,恰好有信服力地说明着代英伦旺盛的创造力和不一般的想象力。
在“人群”这样一个具有哲学内涵和取向的主题上,勿需移植、挪用国外现成的图像、符号,凭藉艺术家对绘画主题的感受、思考和对个人性艺术语言的提炼、概括,实现水墨艺术对现代生活感受和人生思考的深刻表达,对人类社会行为和人性的揭示。这一点,是代英伦的艺术所给与我们的最大启示和信心。